每到三月,朋友圈就被“春光易逝”“花开荼蘼”刷屏,看似文艺,实则千篇一律。原因有三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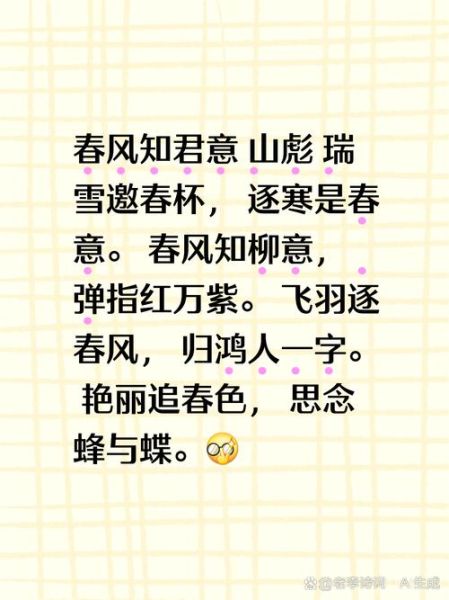
问:春天万物复苏,为何反而触发惆怅?
答:因为“生长”提醒了我们自身的停滞。去年埋下的种子已破土,而我心里的计划仍搁置;去年同行的人已天涯,而我仍在原地。叹春,其实是借景照见自己的未完成。
别急着铺陈颜色,先找到一处只属于你的角落。我曾在老城区的菜市场看到一筐沾泥的春笋,笋壳剥落时发出清脆的“啪嗒”声,像谁在拆信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:春天不是远方山野,而是日常裂缝里冒出的倔强。把镜头对准这样的细节,陈旧的意象就活了。
与其写“又是一年春”,不如把两个春天并置。写今年梧桐刚抽芽时,想起去年此时在医院陪护母亲,窗外同一株树的嫩绿被消毒水气味衬得刺眼。时间的落差自带张力,读者会跟随你完成情感运算。
刻意捕捉不合时宜的画面:写倒春寒里穿短袖的少年、写花树下争吵的情侣、写深夜便利店仍卖关东煮的春天。当温暖与凛冽同框,叹春就不再是单向度的“惋惜”,而成了对生命复杂性的凝视。
凌晨四点,楼下的24小时洗衣店还亮着灯。滚筒里搅动着一件校服外套,领口有圆珠笔画的樱花——显然出自某个赶作业的女孩。玻璃门上呵出的白雾,把街对面的海棠映成一片模糊的红。我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,也曾偷偷在课本边缘描过同样的花,却被数学老师没收。如今我三十三岁,数学公式全忘光,却仍记得那朵花被撕碎时的声音。
原来我们叹的不是春去,而是那个来不及好好画画的自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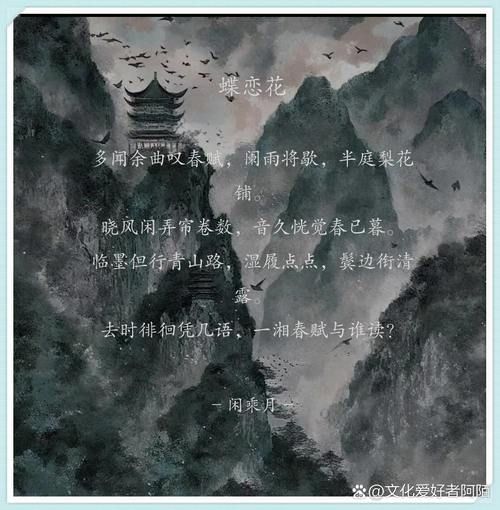
别急着把春天写成诗,先让它把你写成诗。当你愿意承认:那些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时刻,本身就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——你的叹春,就再也不怕和别人撞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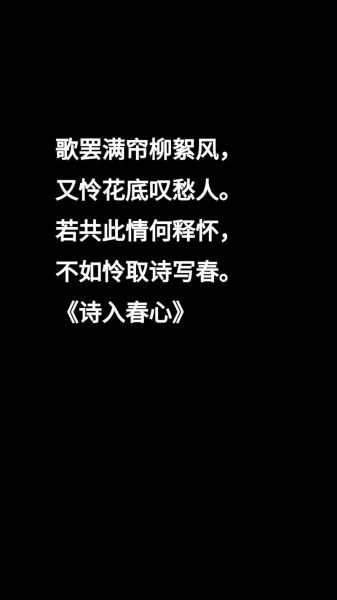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